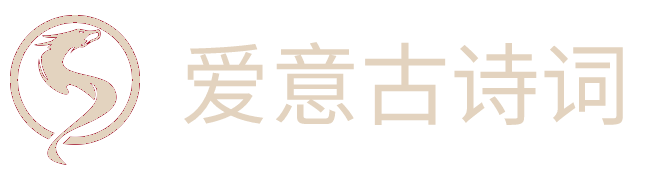苏轼、苏辙,千古兄弟情,世世为兄弟,来世缘未了。两人同志相知,文才卓绝,却时常遭遇世俗压力与命运变迁。他们用诗文书信传情达意,以笔墨情谊长存于历史长河。如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往往易薄易断,而他们之间的深厚兄弟情谊却永远流传,启示后人不忘初心,珍惜友谊。
他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字子瞻),这话他对很多人说过,他最喜欢的散文家却是苏辙(字子由),他很少跟人讲起。他承认他最初是通过苏轼才知道的苏辙,他没办法不了解苏辙,因为翻开苏轼的诗文,写得最好的那些,大都是写给苏辙的,这个小他三岁的弟弟。那些往来唱和的诗词在苏轼和苏辙兄弟一生都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交织的诗词使他们各自成为了对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轼苏辙兄弟出生在四川眉山,从小兄弟俩在父亲苏洵教导下读书。后来苏辙在苏轼的祭文中回忆了这段幼年相伴的成长生活:“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以是终。”寒来暑往,苏轼带着苏辙一起读书习字,不荒废一日。“寒暑相从,逮壮而分”,这样相伴的生活直到成年后才分开。也许是这种幼年一起成长的经历,才造就了他们兄弟之间深厚的感情。
苏轼与苏辙学成之后在家乡同年娶妻,后又跟随父亲出川,又同年一起考进士、应制举,双双得中同榜进士、同榜制举,一直到入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苏轼个性鲜明,旷达洒脱,苏辙则沉稳内敛,虑事周全。兄弟俩形成明显的互补。所以他们的仕途虽然坎坷有异,而相知相亲,始终如一。当官后,兄弟二人宦海漂泊,聚少离多,书信、诗词便成了兄弟联络感情的工具。
嘉祐六年,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二岁的儿子苏迈前往凤翔任官,苏辙送兄嫂出汴梁,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兄弟之间的第一次离别,苏轼登上高坡目送弟弟渐行渐远,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聚散的无常与感伤,写下了著名的诗篇《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辙日后在《逍遥堂会宿并引》中说,苏轼写“夜雨何时听萧瑟”,是因为兄弟少年读书时,读到韦应物的诗句:“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深有感触曾相互约定将来仕途勿恋高官,早日退隐,共践前约,以免妨碍弟兄欢聚。夜雨对床的约定却宿命般成为了兄弟两人后来一生中想而未能实现的梦想。
同年苏辙寄诗《怀渑池寄子瞻诗》,苏轼亦和韵作《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熙宁四年,因变法问题,苏轼被调任杭州任通判,苏辙也上札,请求外任。三年后,因为苏辙在济南任掌书记,苏轼请求去距离济南较近的东州太守未得,后来被批准去了山东密州做太守。两地相距并不遥远,而别离六年仍无法相聚。熙宁九年的中秋,苏轼想起这个六年没见的弟弟,难耐离合之感,写下那首最有名的中秋词《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后人评语:“中秋词,自此一出,余词俱废”。
第二年,苏轼再次调任。赴任途中,两人才得到机会在徐州相见,距离上次分别已有7年。苏辙有感作词:
水调歌头·徐州中秋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苏轼见弟弟悲伤亦做水调歌头以和之: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此后许多年,起起沉沉的仕途中,为表思念之情,苏轼几乎每到一个地方,就给苏辙寄信赠诗,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就超过百首,“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等等。而苏辙每收到苏轼的信都会做诗词唱和以回复,他们不仅是兄弟,更亦师亦友,仕途上也是同进同退。
苏辙一直非常敬爱自己这位才华横溢的哥哥。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在嫂夫人的祭文中也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苏辙认为苏轼不仅是自己的兄长,更是自己的老师。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讲:“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比自己的好,但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苏辙性格低调深沉,他的文章风格就像他的为人。事实上,苏轼有些诗文愿意给所有人看看,有些诗文只愿意给苏辙看,因为那些不愿意给外人看的诗文,他觉得只有他的弟弟最了解中间的内涵和情感。
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自度必死,写下绝命诗《狱中示子由》: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
生死关头,夜雨对床的约定浮上心头,苏轼为自己不能遵守约定而伤怀,写下来生再续前缘的承诺。这世上的男女之间有缘无分时常有来世重逢的愿想,但像这种来世再做兄弟的约定历史上确实并不多见。
苏澈得到苏轼入狱的消息后,即上书皇帝,请求朝廷削去自已官职以替兄赎罪,其《为兄轼下狱上书》写道:
“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
……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非敢望末减其罪,
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在苏辙等人的多方合力救助下,苏轼才得以保住性命下放到黄州做了团练副使,苏辙却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贬江西。出狱那天,兄弟二人百感交集相对无言,苏轼正要说话,苏辙却马上捂住嘴巴,用眼神提醒他:“口舌之祸”!大多时候苏辙更像苏轼的大哥,不但常常提醒苏轼注意官场关系,而且对苏轼从不吝物质资助,“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对于这个总让人提心吊胆的哥哥,苏辙从来没有怨言。苏轼能够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那么洒脱,不得不说,是苏辙替他承担了太多世俗生活中的琐碎与不堪。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苏辙也因哥哥牵连被贬雷州,兄弟两人相遇于藤州,同路一个月往南至徐闻。当晚苏轼痔病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一夜陪伴着苏轼,为他诵读陶渊明《止酒》诗,劝苏轼戒酒。第二天一早,苏辙送苏轼渡海,兄弟二人都想不到这竟然是兄弟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三年后,苏轼被赦北返,因一路舟车劳顿,至常州病逝。苏轼离世前对身旁好友钱济明讲:“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噩耗传来,苏辙悲恸之极,在铭文中写道:“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次年苏辙按苏轼遗愿“即死,葬我嵩山下,予我为铭”,将兄葬于河南郏县。苏轼死后,苏辙把苏轼家人迁至一起以为照应,晚年退隐,终日默坐,谢绝宾客,不与时人交往,其诗感叹:“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
有时他常常想,人生天地间,手足有几人?长大后,即便是再亲密的兄弟姊妹,相聚的日子总是不多的,岁月匆匆,转眼逝去,更何况苏轼苏辙兄弟,仕宦困顿,天南地北,在一起的日子更是少,但是,兄弟二人的感情并不因为距离的远近而产生隔阂,反而是愈久弥坚,愈远愈深!“患难之中,友爱弥笃”,兄弟情深,确实令人感叹。大概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忽略了有一种叫手足的情感。它不同于爱情,不管感情深浅,它都是一生的牵绊。它不同于友情,不管相隔多远,一有紧急困难可以随时寻求帮助,而且只需承担最小或完全不必有的心理负担。它也不同于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一起长大一起变老的经历,有了很多如朋友般互相学习的语言。漫漫人生路上,当父母慢慢老去,当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当周遭的人情关系越来约复杂,当要承担的责任越来约多,有相知相伴有事可彼此商量、共同承担的“手足”,那是多么大的幸运!如果这个“手足”恰好还是良朋知己,一生更有何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