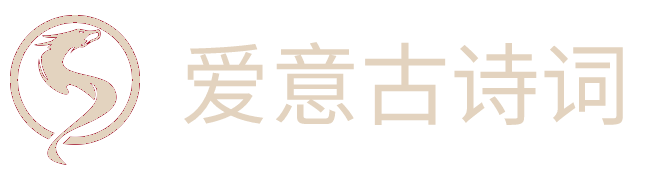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与王阳明被誉为理学与心学的代表人物,二者皆为儒家思想的代表。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理性思维与实践的重要性;而王阳明则强调“知行合一”,主张通过内心直觉来实现真正的道德与智慧。那么,在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中,谁更贴近我们的内心?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今天这篇文章有点长,如果你有耐心从心即理的角度花个五六分钟的时间来认真阅读一下,便可知理,这就是格物致知,但还不一定能达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乃至致良知。朱熹和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集大成者,前者在南宋集理学之大成,后者在明朝集心学之大成。就时间维度而言,谁与今天的我们更近,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精神上我有一些看法,下面我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 一)朱熹强调“存天理,去人欲”,讲求“格物致知”。
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朱熹是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大圣人。他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成为封建士子(而非皇帝)修身的准则;他的理学思想被公认为“天下之真理”,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同时也作为封建王朝对人们(同样不包括皇帝)思想行为的规范准则。
朱熹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叫做“道”,即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洞悉了道,就可以洞悉世间一切。
朱熹把世界分成两块,一块叫“理”,一块叫“欲”。他认为“理”存于万物中,但“理”有一大敌,那就是“欲”;所以要想“存天理”,就必须“去人欲”。
在践行上,怎样才能做到存天理、去人欲?怎样才能悟道?朱熹提倡的方法是:格物致知。格,即琢磨的意思。只有不停地格物,与事物紧密接触,才能明白其中包含的“理”;在这个过程中,还得要去除人的一切欲念。
朱熹终其一生,虽为仕不多,但也曾在其任上勤政有为,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他还改建、扩建了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但朱熹在奉诏进讲《大学》时,却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区分清楚授课对象,自顾自地在那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滥用,这就引起了宋宁宗和宰相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一个半月,便被宋宁宗内批罢黜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朱熹是个做圣贤的人。可惜的是,他成也圣贤,黜也圣贤。
(二)我所崇拜的王阳明强调“心即理”,讲求“知行合一”。
即“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实践过程;“致良知”是根本目的。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又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的哲学思想在明代影响最大,并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有趣的是,王阳明早年却是朱熹的一个超粉,他起初的理想就是像朱熹那样,做圣贤。
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故事,说的便是王阳明在他21岁那年,读完朱圣人著作后,便邀请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两人端坐院中一棵翠竹下,目不转睛盯着竹子,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格了三天三夜,朋友晕倒了。格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晕倒了。苏醒之后,王阳明喟然长叹:“圣人之说可疑也!”
后来又经历了一件事,让王阳明开始全面怀疑朱熹之学。他在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僧人正在闭目打坐,据说已不视不言三年。王阳明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冷不丁大声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和尚给惊动后,睁眼应了一声。王阳明继续盯着他问:“家中还有何人?”和尚答:“老母尚在。”王阳明又问:“你想念她不?”和尚没有即刻回答,过了一会,面有愧色地说:“怎能不想啊!”和尚的回答,让王阳明顿时陷入沉思,这个僧人即便苦修至此,心里也仍存思母之念想,何况凡人?王阳明意识到,凡为人者,皆有欲念;人之欲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泯灭。朱熹之说,不符合人性。
这两件事,对王阳明思想上打击甚大,他原来一心要做圣贤的理想就此破灭。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在二十八岁时参加了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后又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阳明上疏论救,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栈驿丞。
路途中,王阳明发现被刘瑾派人追杀,遂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随后继续上路,来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王阳明来到这个当时还未开化的地区,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他自己也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自食其力。在这段时期,他对《大学》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王阳明顿悟的“道”,是“吾心之道”,即每一个人都具有“本心”,这个本心实际就是生命的本原。人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诸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恶、判断推理,就在于人具有这样一个“本心”。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吾心即道”,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天理”与“人欲”原本就存乎一心,并不能两相分割。从数学概率论角度来说,阳明之理易于传播,基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并由此发展起了“心学”。
在践行上,王阳明提出的方法就是要“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不仅要认识“知”,更应以“行”实践“知”,只有把“知”“行”统一起来,才称得上“善”。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应去付诸实践;实践符合这个道理的“知”就是真知;若实践与道理相悖,那“知”就不是真知。
在“知行合一”基础上,王阳明又进一步提出“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他的心学理论体系:“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也就是说,“天理”就在每一个人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去提高内心修养和智识;去除私欲杂念的纷扰,从而达到社会和谐运行,这就是“致良知”。“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实践过程;“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大千世界,纷繁复杂,但人们只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致良知的前提下,知行合一去践行,则人人皆有成为圣贤的可能。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就是要内圣外王,将心性之学转化为卓越的事功。他将自己的心学理论付诸实践,屡屡使用心战,荡平江西为害数十年的盗贼匪患、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总督两广抚平盗匪。尽管终武宗一朝,王阳明平叛之功未得到朝廷封赏,但世宗即位以后,王阳明又得以加官晋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还极大影响了东亚无数豪杰。1905年,率领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俄国海军,开创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先例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在日本天皇为其举办的庆功宴上,面对众人一片夸赞之声,却高举起一块腰牌,上面写着七字:“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学的高濑武次郎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日本之所以能迅速窜升与欧美列强分庭抗礼,一切都归功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阳明心学。连国父孙中山也曾说过:“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三)“成圣”之路,朱熹做“加法”,王阳明做“减法”
但“成圣”的道路,不同时代的儒家,或不同的思想大家,他们之间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朱熹和王阳明之间的分歧所在,并集中体现在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分歧上。朱熹认为,成圣之道要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而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是圣人,只要不断祛除蒙蔽内心的东西,重新恢复人心的初始状态,自然就成圣了。
简单来说,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成圣之道就要向人心外探索“理”,不断做加法;而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认为,心本来就有完备的“理”了,不要向外求索,而要向内求,做减法,不断地发现和去除不良的欲望,存样原本优良的品性,那就对了。
在朱熹、王阳明之前,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北宋的程颐。程颐认为,“知者吾之所固有”,而“致知在格物”。意思是,人本来内心是有“知”的,但要致知,非通过格物不可;格物就是“穷理”,大概是说探索一切事物的“理”直到尽头。穷了理,自然就“致知”了。
朱熹、王阳明都深受程颐的影响,他们继承了知是人所固有的观点。但对于何为格物、何为致知,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朱熹继续发扬了程颐的观点,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他的意思是,人的心灵都是有知的,而万事万物也都有一个“理”,要对外穷尽这个理,才能对内发掘那个“知”。
王阳明对此有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朱熹。他说,人的心灵都有“知”,这是对的,他还特别提出,知就是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但要说万事万物有“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理根本不在于万事万物上,而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头。每个人的心,就是完善的理。也就是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和朱熹,隔着342年。而这场对儒家经典典籍的跨时空学术之争,到今天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人们至今对格物致知的意思依然没有明确,或者说,也无需明确。但是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更喜欢王阳明的观点。
我们每天面对着庞杂的信息,他们从各个终端来到我们的眼前,无数碎片般的漂浮物,像地球外太空的垃圾,不仅阻碍我们见到真实的世界,并且还塑造着一种混乱的思维和行为的模式。在这个时代,从喜怒哀乐的小情绪,到对成功、失败的理解,再到对生命目标的追求,都是飘忽不定的。
我们被与我们无关的信息刷屏,每天花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茫然而焦虑地盘手机,试图通过信息的扩充来获得无用的安慰。虚拟的体验,不断侵蚀真实的感知,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一个王阳明来提醒我们,人的内心本来是完善的,当我们拨开那些多余的遮蔽和纷扰,大胆地去伪存真,就能获得更有质量的生活乃至生命。
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格物致知吧。
(四)传承与践行:谁与我们更近?
综上所述,不辩自明。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历史人物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但扬弃和传承其思想精神,却应超越其历史的局限性。黑格尔也说过,“真理是在漫长的发展着的认识过程中被掌握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都是它前一步的直接继续。”
朱熹和王阳明,他们的学说思想和践行方法,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都是中华文明悠久的文化积淀,都有着跨越时空、超越国度、与时俱进而日久弥新的生命力,也都能为国家持久发展、兴旺发达提供不竭动力与重要支撑。
但若比较二人的思想精神内核、践行方法与实际效果,可以看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朱熹认为“人欲”是可以去除也必须去除的;而王阳明则认为人欲不可能去除,但可通过“致良知”以尽可能减少人欲的干扰。
比如现在我们实践的“点点阅读”,就应该去除人欲的干扰,而不是做阅读假像。只要我们格物致知的真阅读,心即理的点滴阅读,知行合一的用心阅读,与时间为友,必然达成致良知点点阅读。
从这个角度看,尤其是基于符合人性考虑的点点阅读,个人觉得,还是王阳明与我们更近一些。你说呢?
时光无声
2022.1.6